2022-09-30 09:44阅读 0
“梅花奖”婺剧文武生楼胜: 把每次演出当成最后一场
本文转自:扬子晚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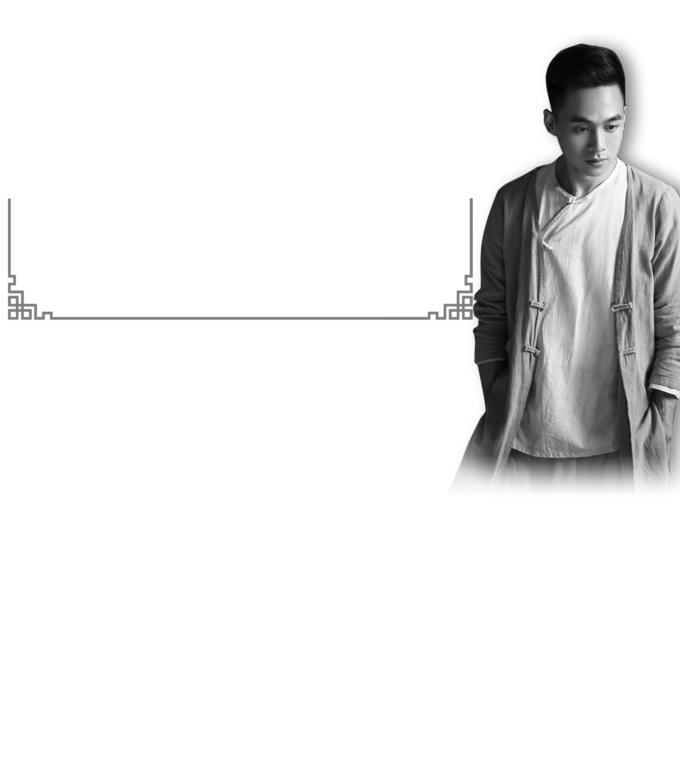

扫码看视频
去年,婺剧演员楼胜在南京摘得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戏曲类的榜首,他的竞演节目也在社交平台引起刷屏,很多人第一次见识婺剧惊、险、奇、绝的艺术魅力。今年中秋,楼胜带着《白蛇传》在江苏大剧院上演“许仙十三跌”,再次看傻了观众。接受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专访时,楼胜坦言,戏曲舞台很残酷,他今年36岁,把每次演出当成最后一场演出,同时也在拓宽表演界限,希望用更多方式留在舞台上。 文 | 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“文戏踩破台,武戏慢慢来”,婺剧就是要“重口味”
对于婺剧在南京上演时引发的社交平台刷屏,楼胜淡然笑说,观众吃惯了南京的盐水鸭,偶尔吃点浙江柴火灶炖的土鸭,也有另一种味道,“婺剧来自民间,很草根。婺剧有六大声腔,无论去哪里演,都能捕捉观众心里的乡情。”
婺剧的戏剧张力很大,既典雅婉转,又高亢激昂,表现力很强,而且有很多抓眼球的戏,“因为它之前是在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表演的,百姓看戏‘口味重’,所以动作要重,表演要夸张,才能很外化地展现给观众。长久下来,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。”
婺剧有句俗语叫“文戏踩破台,武戏慢慢来”。楼胜解释说,一般来说,文戏应该是细腻的,但婺剧不同,要让观众感觉过瘾,文戏就需要满台跑,要有情绪起伏,节奏感要生动而强烈。
而武戏呢,却要静下来,为了让观众看到细节,就要增加动作的造型雕塑感,同时充分展现人物内心,不能毛毛躁躁,要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剧情,比如,谁被打败了,得让观众看到被打败时是败在哪里。
拿《白蛇传》来说,白蛇青蛇和楼胜饰演的许仙,在追、打、逃、跌、拦、挡等关系中形成了各种造型,在逃的许仙内心是恐怖、惊慌,外部表达是连滚带爬,用的是高难度的跌、摔等技巧。再比如,当白蛇责备许仙轻信法海之言时,既爱又恨地用手指点了一下许仙的额头。许仙没有提防,跪在地上顺势向后倒下,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地;等白蛇做扶起许仙的动作时,他又立即从地面弹起身体。“这一点、一倒、一搀,前后不过十多秒,很多剧种都有这个过程。其他剧种的许仙并不真倒下,只是略微后仰而已,而婺剧里的许仙是真的倒下并迅速弹起。”
楼胜说,婺剧这些大开大合、大锣大鼓、大红大绿、大吼大叫、大蹦大跳的表演特点,都来源于民间,就是要让观众看懂听懂。
不少绝技绝活失传,他试着改良一些恢复一些
婺剧文戏、武戏的特点如此鲜明,也造就了很多鲜见的绝技绝活,比如,蛇步蛇行、飘若纸人、大眼小眼、蜻蜓点水、吹脸抹脸、踢鞋穿鞋等等。
楼胜以《火烧子都》介绍说,戏里有婺剧老艺人传下来的抹脸、吹脸技艺,是人物内心浓墨重彩的表达。“以前没有灯光,演员在庙台、广场演出,观众多,又离得很远。公孙子都是惊吓、抑郁而死,他临死时的情绪,演员用表情已经不够表达了,他们怕观众看不清楚,就创造了抹脸、吹脸。颜色是一层一层抹上去,人物内心是像笋壳一样,一层一层剥开来。一抹,是煞白,吓的;又一抹,是血红,憋的;再一抹,黑的,面如土色;最后,灵魂出窍,脸喷成了金色。”
楼胜的行当是“文武生”,吹脸抹脸、踢鞋穿鞋这些都要掌握。他坦言,不少绝技已失传,他看了很多资料,也到别的剧种学习借鉴,恢复了一些,也改良了一些。
“婺剧人生”并非坦途,练功太苦,也想过逃跑
说到婺剧,楼胜侃侃而谈,回忆自己与婺剧结缘的那些节点,楼胜仍很感慨。他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南端的一个偏僻小山村,看婺剧是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,“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,我天生喜欢婺剧,认为它是最好听的戏。但要让我说为什么喜欢,还真说不出。”
楼胜读初一那年,武义县第二职校婺剧班(后并入兰香艺校)到学校招生,一眼就看中了他。楼胜文化课成绩不错,因此老师和一些亲属都反对他上婺剧班,但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。
进戏校后,每个星期六回家,家里会给他带上一袋米、一罐梅干菜、一双白球鞋,因为一星期肯定要练废一双鞋。回忆当时练功的苦,楼胜坦言,想过逃跑。早上天不亮就开始练,下午还有文化课,晚上又是一堂扎扎实实的练功课,“太痛苦,太枯燥,太累太疼。一堂又一堂,像跑马拉松。”楼胜很坦诚地告诉记者,也哭过,很多基本功练起来真的像酷刑。
毋庸置疑,戏曲里的很多绝活都是在挑战人类的身体极限和意志力。比如,戏曲中的“僵尸”,是一种摔打功夫,要求人物僵着倒地,演员往后一摔,像一块门板倒地,常常会博得满堂彩。然而,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本能,正常人摔倒前一刻会下意识地蜷曲身体,而戏曲演员必须对抗这份本能,让身体放弃自我保护,这在心理上也是极难克服的一关。楼胜在《白蛇传》里就有“僵尸”这个动作,有文艺评论家曾评价楼胜扮演的许仙,“屁股坐子、摔僵尸、跳着躺横僵尸、跳着跪……每一下看得人都要惊叫,又高又飘又标准,就像拿命在演出。这让我心里竟然难过,这样的演员,这样地演了无数场,每一场大概都满身淤青吧?”
记者好奇地问他“真的没有保护措施吗”,楼胜说,“没有,头部也没有。无数次练,常常摔得晕乎乎”,传统戏曲里确实有很多充满挑战的内容,包括戏曲服装、盔头翎子这些,都会给演员带来无尽障碍,需要不断磨合和练习,形成肌肉记忆,同时正因为有难度,才能震惊观众。
这次来南京演出的《白蛇传》中,“许仙十三跌”常常看得观众于心不忍,心痛演员“以戏为命”。高难度动作是其次,楼胜却向记者道出了他更多的解读。“十三跌并不难,很多武生演员都能做到。难的是,要结合许仙这个文小生行当。”楼胜说,许仙不是武将,每一跌都应该有层次,才能跟剧情、跟人物捏合好。无论是他慌不择路,还是脚底打滑,都要让观众觉得是会真实发生的才行,所以许仙每一跌所起的劲儿也应该不一样。
圈内少有的“梅花奖夫妇”,对彼此艺术的要求更严苛
《白蛇传》里,白娘子口中责怪、心中不舍、手中揽护;小青爱恨分明,真心喊打喊杀。许仙见白娘子回心转意,讪讪地这边厢一凑,那边厢小青一嗔,他赶紧扑通又跪下了……很多戏迷会心一笑,因为台上不依不饶的那位小青,就是“许仙”在现实生活中的妻子——第27届“梅花奖”获得者杨霞云。
圈内的“梅花奖夫妇”并不多见,楼胜表示,妻子练功比自己还勤奋,两人一起练功一起巡演。他们俩合作的作品挺多,除了《白蛇传》,还有《穆桂英》《昆仑女》等,今年还有新排戏《踏摇记》。问起合作中间有没有争执,楼胜笑说,当然有,甚至争执还相对多一些,对彼此的要求反而更严苛。
楼胜的严苛还体现在舞台的方方面面。他认为,妆面、头饰、服饰等也是演员塑造人物的一部分。服装要与故事情境、人物身份、文化底蕴等相符,配色的明暗,花纹是金线还是花线来绣,都要讲究相称,“我更了解我要塑造的人物,所以每个人物的服装制作过程我都会参与。我还学习了绣花,研究戏服的制作过程,这样才能与戏服设计师沟通。”
“剧组有没有说你很难搞?”楼胜笑着回答记者这个问题,演员都是难搞的,如果演员很好搞,那这个戏就不太能搞得好,“我有我的坚持,就是舞台上不能马虎”。
一方面是对舞台呈现精益求精的追求,一方面是年纪增长带来的体力和柔韧性的衰退,采访中,今年36岁的楼胜多次流露出“职业焦虑”,“等我做不了‘十三跌’,我还能做什么?”他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,“所以我特别珍惜现在的每一场演出,我总把它当做是最后一场来完成。观众百忙之中来看戏,我希望能让观众坐下后就不想走,甚至下次再来看,这是我们演员该做的。”
快问快答
在南京拿到梅花奖,对南京的感情如何?
南京是我的福地。去年竞演时南京很热,我的折子戏比较累人,体力消耗大,没想到演出当天温度骤降,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。
你上过两次春晚,多次登上央视,这些年很多荣誉在身,压力大吗?
荣誉与压力共存,得到了很多,就应该付出更多。
今年你还跨剧种拜师了?
对,有一句话让我很受益,“京昆打底,剧种立身”。今年3月,我拜师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瑜。这些可以让婺剧表演变得更大气更专业,我也在拓宽自己未来的戏曲之路。
下一代也喜欢婺剧吗?
女儿还很小,不过她每次看到电视里有小生、武生的戏,就觉得这个应该让爸爸演。
这些年婺剧的巡演计划如何?
其实排得蛮多的,还要参加省运会、亚运会的排练,一个接一个。婺剧的曝光率在增多,包括采访、发言这些,其实我做起来并不得心应手。但只要时间能挤一挤,我都尽量来说一说,毕竟这也是我们与观众、与读者交流的一个桥梁。也许他们看了我的专访,就会在心里埋下一个种子,以后的演出就会增加一个观众。这对我们来说,也是非常幸运的。
我要反馈

 赞赏Ta
赞赏Ta 赞赏Ta
赞赏Ta